我们在哪里失去了它
--约翰·列侬时代的美丽
●欧文将会遇到什么人欧文走在七十年代初的东京都旧城狭窄的街道上。一家爵士乐的酒吧,在街边招摇着一份略显迷离的喧闹,走过去,一切就又都回复到那种古旧的氛围中,就像什么也没出现过。那家酒吧的老板是一个叫村上春树的日本作家,他目睹了青春在那个年代里的所有狂放和沉寂,他记录了下来。欧文从那里开始结识了几个很青春的人,有的人永远17,有的人永远20,有的人慢慢地老去,就像我们。
约翰·列侬的旋律已经开始了,《挪威的森林》,和我们每次听到的一样。
●欧文的问题
众多的可能性是让我们来选择的吗?
爱是一种心碎吗?
死是生的一种存在状态吗?
●故事
那是五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渡边能不能不上课,一起去打桌球。渡边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趣,便出了校门。他们玩了四局。第一局渡边赢了;后三局木月赢了。玩球的过程当中,木月显出很不合他性格的认真。“今天我可是不想输”——这是木月对渡边所做的唯一的解释。几个小时后,木月在自家的车库死了。自杀。渡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两年半之后的一封信里他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最后一个球的情景。那其实是一个需要相当冲击力的难球,我以为他不至于一举成功。然而大概是一种巧合吧,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毡垫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信是写给直子的,直子是木月青梅竹马的女朋友,这封信不久之后直子死了。自杀。
现在我觉得有必要跳出来一些讲述这个故事,因为它很伤感,在所有的伤感当中有什么比青春的伤感更让人心碎的呢?我不想这样。我希望能够像欧文那样站在另一个地方看--当年村上春树都是在远离东京的希腊完成的这个故事。
那好,我们看一看我们都能看到什么。
在一年之后,渡边告别了红球绿毡还有木月桌上的白花,到东京的一所私立大学上学,住在一个古怪的寄宿所里,他的同屋因为与众不同的习惯常常被人称为“敢死队”,有一天他一个人走了,走前送给渡边一只荧火虫。他还有一个同样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朋友,名字叫永泽。永泽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一方面他有一远大的事业--记住,不是理想--可作,另一方面他有坚忍的性格,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女孩子有致命的吸引力。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渡边很荒唐地在东京阴暗的小街里与女孩子调情,甚至躲在哪个小旅店里,那多半是因为永泽的缘故。除此之外渡边的生活很平淡,就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样,他不爱上课,但他把那当成锻炼自己忍耐力的一个机会。
有一天他在电车上遇到了直子。直子和他一样都是为了逃避木月的死而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没有熟人的学校的。在这里需要回过头来说一下,直子和渡边在木月活着的时候同样是好朋友,这很关键。在陌生的地方,两人相遇了。
然后是不停地走,说话,聊天,所有不着边际的、小心翼翼的、青春的话都在那个夏天说了,当然也有死亡,也有恐惧,就像天空不总是晴朗。在走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被忽略了,有些东西被夸张了,有些东西从无中产生了--我说的这些都是爱。在直子20岁生日那天,爱吞没了这两个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渡边的生活从不停地走变成了不停地等和不停地写信。直子不辞而别了,留下了渡边,继续锻炼他的忍耐力。
有一天,直子回信了,她说她写信很费力,她说她在京都一座山里的疗养院里。
直子在我们的眼中一下子变得很远了,确切一点说,她精神失常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头绪有一点乱,我们只好抓住渡边,看他的日子。让他带着我们去经历那一段颤栗的青春。
中午,一个很庸常的中午,一家小饭馆里,绿子出现了。有许多男孩子喜欢这个人,也包括欧文--在一个充满了感伤的故事里,有一袭很清很轻的风飘进,总是让人很放松。真的像一阵风,绿子坐在渡边的对面:我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
绿子有一个姐姐,除了与渡边通过几回电话之个,她在这个故事里可有可无,绿子的妈妈在一年以前去世了,绿子的爸爸最初的说法是在乌拉圭,后来我们发现,绿子在这个问题上撒了一个小谎,他只是一个病人,渡边曾经在医院里看到过他一次,那可能是这部小说里最有世俗人情味的一段,在那之后不久,他也去世了。--生活就是这样,总是有人出现,又总是有人告别,告别的时候有些伤感,但谁又能说出现的时候不是孕育着伤感的出现呢?渡边在一个午后,在绿子家的屋顶上看邻居家失火,他们唱着歌,喝着啤酒,天空上有直升机,他吻了她。这个故事变得不一般了,或者说变得痛苦了。
那个时候的渡边还不到20岁。在他不羁的生命当中,虽然没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但他每时每刻都必须面对生命对他的考验。人选择了不羁,可能就意味着自己得承受一些什么--在聪明人的世界里,人得有人的尊严,这是一个公理。,而尊严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渡边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尊严?
渡边当然知道: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木月的死。“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冷风乘虚而入。对于我,木月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但百思不得其解。我所明白的只是:由于木月的死,我的不妨称之为青春期的一部分机能便永远彻底地丧失了。对此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和理解。至于它意味着什么,将招致何种结果,我却如坠云里雾中。”渡边真的不知道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东京街头一个荒唐的夜过去之后,疲惫不堪的渡边回到寄宿所,他发现了直子的信。发自那座疗养院的。直子恢复得很好。她邀请渡边去看一看她。那难以割舍的感情没有让渡边有半点迟疑,循着那地图去了。那是一个叫“阿美寮”的地方,取自法语ami--朋友之意。
在山上。走了很远的路之后,渡边遇到的第一个人是玲子。一位中年女性,直子的同室病友,一位很健谈,很善良,很年轻的人。她是我们大家的朋友,玲子一出现就给人这种感觉。
她有她的过去,她有她的不幸,这样可以让我们稍稍感受到一点平衡,不至于让我们在那个叫“阿美寮”的地方把自己给忘掉。
她出现了,像女小学生一样剪着整齐利落的发型,一侧仍像以往那样用发卡一丝不乱地拢住。看去宛如中世纪木板画中经常出现的美少女。终于又见面了,在这异乡,在这当初谁也想像不出的地方,在这个多了个玲子的地方。
天晚了,灯熄了,一枝蜡烛燃起了。音乐也响起了。那是玲子的吉他声。“弹《挪威的森林》。”直子说。玲子拿出一个贮币盒,直子向里投了100元的硬币。这是规矩,因为直子太喜欢这首曲子了,才特意这么做,表示打心眼里喜欢。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渡边也拿出了一个100元的硬币。
“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一个人孤单单的,又冷,里面又黑,又没一个人出来救我……”直子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首曲子拿出那一百元的硬币。木月,一个死去的人,他们共同的朋友,成为一个话题。直子说她总是碰到这样的事。于是我们知道了,在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她回家……
她的姐姐,那个刚强而且能干的姐姐在家中上吊自杀了。
我不知道村上春树写到这里的时候,是否感到一丝寒意,是否感到自己笔下的世界太冷酷了--一个接一个的死亡,一个连着一个的痛苦经历,脆弱的直子怎么能承受这样的灾难?但在一个不羁的年代里,在一个纷乱的世界里,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面对的就是这种炼狱一般的锻冶。
两天之后,渡边回到东京。绿子又出现了,这个风一阵的女孩总是用很快的语调说话,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幻想当中,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总是让渡边感受到生命中那种踏实的立体感--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动,在摇撼他的身心--渡边一天一天地与自己的寂寞和无助作着斗争。那可能是最忠实也是最按部就班的一段生活:“尽管我有时寂寞难耐,但基本上还是活得满有兴味的。如同你每天早上侍弄小鸟和在田里做活一样,我每天早晨也都在拧紧自身的螺丝,爬起床就刷牙、刮胡子、吃早餐、换衣服、走出宿舍大门。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般要‘咔咔’地拧三十六下螺丝。并且想:好,今天要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
这同样是写给直子的,同样是在这个时候,渡边的心情有了变化,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给他的越来越紧迫的压迫感。那是来自绿子的。
绿子还在欢唱着度日,但她不再无忧无虑,她想得到,就像她最开始时说过的那样,她想得到百分之百的爱情。歌声还在耳畔,而渡边却不能仅仅是倾听了。他需要作出回应。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可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它和我们的整个故事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不得不停来说它。有关永泽的,永泽是一个有魅力的男生,这一天他考取了外务省的一个职位,向着他的目标又走近了一步,现在他需要做的是离开那个叫初美的女孩子。像很久以前的木月、直子和渡边一样,这三个人在一起吃饭,而到了晚上,最后送初美回家的是渡边,在路边两人一起去打桌球。那是两年半以后渡边的第一次--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一次。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几年以后,初美割腕自杀了。这个游离于我们故事之外的女孩子,最后走的是同样一条路。
在那之后不久,渡边又去了一次阿美寮。
1970年到来的时候,渡边搬出了他生活了两年的寄宿所,在郊外,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还期待着直子能够康复能够和他一起在这个小屋里的新生活。他在房门外钉了一个邮箱--但是没有信来--直子的病加重了。后来玲子来了一封信证实了这一点。那是春天,一切生机盎然,渡边坐在廊下,想思考点什么,但什么也思考不好。
绿子说: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作“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复原状。绿子生气了。渡边发觉自己的生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另一个世界了。在经过四月和五月春天难耐的寂寞之后,渡边下了决心。他给玲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他的选择:绿子。
没过多久,直子便死了。按玲子的说法,这与渡边无关。
渡边经过了一个月的流浪生活,回到东京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玲子出现了,他们为直子准备了一个葬礼,就像那次在阿美寮一样,玲子唱了五十一首歌,这里,当然也有那首《挪威的森林》。
是木月的终归还给了木月,曾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曾经尽了那么大的努力,直子还是到了木月的身边,想必直子也是希望这样的选择吧。“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自己本身负责那里的管理。”
绿子家的电话响了,绿子沉默了很久:“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渡边自问。是啊,这个人他在哪里?
●欧文与村上春树在一个小酒馆里的对话
欧文满面泪痕,这一点也不奇怪,他本来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坐在一家小酒馆里,村上春树耳朵里塞着一个耳机,欧文很大声地跟他说话,村上不时疑惑地抬起脸,带着一种询问的表情。欧文知道他还在听约翰·列侬的歌,那个时代是他的青春时代,他离不开。
“生活就是这样,你可能觉得这里面充斥了太多的死亡,感觉到一种偶然,但实际上生活就是偶然的,当你开始思考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秘密。”村上同样大声地说。“可是我感到一种压抑,不是你的故事,而是你对可能性的蔑视,你没发现吗,每个人都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的,但你太吝啬了。”欧文说。
“还记得那句话吗:在周围充满了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话,可它是让你选择的吗?它只是让你无法选择,只能在一条路上走下去。渡边也是一样。”村上的意思是说可能性越多你越无法选择。
欧文呷了一口很烈的酒,他不想这样,但是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从那种氛围当中出来,“我可以不喝,因为有很多种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但我只能这么做?”“对,你只能这么做。这是我所喜欢的,同时它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他们不羁生活的背后,是一种极其平常的一些东西。”
“那是什么?”欧文头有点晕。
“追求幸福。就这么简单。”
所有的心碎,所有的感伤,所有的不羁,所有的混乱之后,都是在追求幸福。“那么爱呢?”欧文可能只是出于一种本能想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终于回到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是青春啊,青春里有爱,它有可能还是全部,而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死呢?你制造了很多死,压抑也许更因为它的存在。”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话我早就说过了。我还要说的是,这就是真实,没有人能制造死,死只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对于一个人来说,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死什么也不是。绿子对死亡的理解可能是最有阳光味道的,这也是我喜欢的。所以你看渡边活着,我也一样。比如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喝酒,听音乐。”村上把耳机递过来,“要不要听一听?”
“《挪威的森林》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这种音乐总是转瞬即逝的。”
音乐在欧文的耳边很强劲地响起来了,于是在欧文的眼中,这个略显颓败的小酒馆变得模糊了,剩下的只是音乐,那节奏一下一下地冲击着他的耳鼓,除此之外他什么也听不见了。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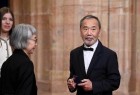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我们在哪里失去了它: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