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的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大概是在日本国内甚至国际上最为畅销的日本当代作家,其国际影响毋庸置疑。他不仅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域呼声很高,这些年也斩获耶路撒冷文学奖、西班牙卡塔龙尼亚国际奖、安徒生文学奖等国际奖项,即使被誉为美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的乔纳森·弗兰岑,也一边表示很难找到让人真心感激的书籍,一边表示非常感谢村上春树写出《奇鸟行状录》(也翻译为《发条鸟年代记》)。
不过村上在日本国内的获奖记录就比较一般了,不仅没有获得芥川奖之类的纯文学奖项,甚至通俗文学奖如直木奖也与之绝缘,这方面甚至不如东野圭吾。好玩的是,村上春树对于日本文学圈甚至主流,一直有点自甘局外人的状态,他的影响很大来自于读者的肯定,这些读者很大意义上是作为弱者的大众,也是村上的影响所在。
在耶路撒冷获奖后那篇著名的演讲中,村上作为一名小说家发声,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职业撒谎者,表态“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村上演讲的义正词严,曾经让我和很多朋友一样激动认同,让我重新思考,站在蛋这边,但是蛋是正确的吗?即使蛋代表着大众,代表着弱者。我逐渐意识到村上观念的倾向是向左,这与他同情弱者反抗体制以及全球化普世情怀也不矛盾。在日本这样一个崇尚集体主义又右倾的社会,村上是一个左派,但是问题在于,有没有个人主义的左派?
在中国语境下,强弱很多时候具备道德意义。很多时候,故作批判却又惺惺作态的陈述,都让我涌起多重的道德反感,既反感其批判对象,也反感批判者,更为自己不能义正词严地站在蛋那边感到抱歉。
《奇鸟行状录》写于20世纪90年代,在当时村上已经用隐喻的方式探索二战问题。说起来,《奇鸟行状录》是我读的第一本村上小说,甚至早于《挪威的森林》。当时大概还是初中,却已经感到作者笔下的张力,与其他作家有些不同。
村上春树 著;林少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有意思的是,我从小读村上,更多的是把村上作为一种都市文学来看待,更多感慨于他对于人性的反思,但是对于社会批判却没有更深入的感受。这次来到日本,才意识到村上的写作是如此具有政治色彩,他对于日本社会的立场与情感,并不像小说表面看起来那么疏离,恰恰充满了关怀,联系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之后他开始写作的报告文学《地下铁事件》,乃至于《1Q84》,行动的意义已经相当明显。
日本社会往往被称为信奉集体主义,但是日常交往中却有所不同,大家往往不干涉不评论别人的事。这种日本人的个人主义和欧美自由主义略有不同,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或者说怕麻烦(别人)。某种程度上,所谓的同调压力,足以构成个人的自我审查。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理解村上文学中的个人化与抵抗,甚至他所谓“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其实更有意思。
美国畅销小说家斯蒂芬·金有句名言:“所有的小说其实都是信件,专门写给一个人看的。”某种程度上,村上的小说应该是写给特定人群看的,当然也包括海外读者,但更多显然是为日本社会而写作。
一次又一次,村上春树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我不意外,也挺好的。
之所以不意外,正如我多次说过的,写畅销书还得诺贝尔文学奖,听起来好像就是太好却不太容易成真的美事;之所以说挺好的,是因为得奖与否实在不是唯一目的,对于眼下有名气、有身份、有畅销保障的村上,多一个锦上添花,少一个来日方长。
不过,村上春树没能获奖,在国内激起的涟漪似乎超过日本,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规则解析再到得主性别、地域、政治解析,就是素日严肃高端的财经媒体也来凑热闹,更有甚者,搞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投票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一谈就俗的话题,难怪人人未能免俗,笔者忝列其中。
目前社交媒体的流行说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得奖之前,主要是感性表达,往往集中于表达远近亲疏,所以中文书籍出版多的尤其来中国多的作家往往被一厢情愿地冠之以热门希望。这是人情,无可厚非,但是相比较国际作家的复杂程度,如此单纯的愿景实在难以匹配文学世界的实在进展。另一类则貌似理性预言,尤其是名单公布之后纷纷显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就像证券分析师们总是张扬正确的预言隐匿错误的预言一样,好像永远手握水晶球。
文学是很私人的事,文学评论更是众口难调,尤其在众声喧哗的今天,所以诺贝尔诸多奖项之中,文学奖大概是各路意见最多而又最漫无边际的一个。
按照微博好友李大卫的说法,大体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热度,和一个人群文化上的外省程度成正比——此处,“外省”这个词语,换作土豪、城乡接合部亦可。更进一步,评价的专业甚至清晰程度,基本与参与人数成反比,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其中一例。
虽然哲学家说趣味无争辩,但品位总是被附加长长的鄙视链条,文学界的势利评论比比皆是。当诺贝尔文学奖偏向众望所归之际,往往会被批评迎合大众,而当诺贝尔文学奖剑走偏锋之际,往往又有批判说喜欢冷门,两害相权取其轻,好像冷门总比大众高端洋气上档次一些,所以个人对最近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实在兴趣不大,不必列入非读不可行列。
爱丽丝·门罗
从82岁的加拿大奶奶爱丽丝·门罗获奖再到英国文坛的“移民文学三雄”之一的石黑一雄得奖,各种新闻总有写头,从家庭主妇逆袭成为热门话题到一下子人人都爱读移民小说,那么让大家继续去谈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继续聊村上吧。
村上的作品,其实为“村上春树”四个字所累,贴上通俗、小清新之类标签后,当我们谈论村上时,往往有过度诠释之嫌,还会面临更大一群不读村上的声音。社交媒体上的村上愈加面目模糊,有前辈说村上的小说不如日本前辈,有年轻作家留言说村上远远不如帕慕克,就连经济学家也在谈论村上作品的色情,很多人批评村上的作品脱离社会,村上还是村上吗?
村上确实不类似他的日本前辈,尤其是昭和一代的文豪,风格也不如帕慕克那般带有东方色彩,情色似乎也是村上作品中自然不过的摆设,以至于常常令人忘了它的存在。不过,我认为这恰恰是村上作品的特点,那就是他的现代性。抽离东京等地名,村上的人物无论放在纽约还是上海,都是栩栩如生的,我觉得对于小说家来说,能够创造出这种都市化的真实,已经弥足珍贵。帕慕克或许比村上深刻,但是我从村上汲取的养分,远多于帕慕克,正如张爱玲所言,现代的东西,到底和我们亲近。
其实考察村上本人,好像除了在美国看到船底的海裙菜忍不住流口水之类细节之外,他带有不少世界公民的气质,无论跑步的生活方式,还是音乐的流行趣味,抑或饮酒的倾向习惯,很难看出特别的日本化因素。村上的前辈中,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东方和传统因素影响不菲,就像颁奖词也强调“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可是,村上不是川端,村上的时代也不是川端的时代。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村上的写作,体现了与世界的共时性,这也是他不仅在日本赢得欢迎,在别的国家也收获粉丝的原因。我以前觉得村上是一位有世界公民特质的作家,后来想想,对于呼吁脱亚入欧多年的日本,本来早就在发达国家的共同体内,我们看村上,和世界看村上,角度不尽一致。
回头来看,这不是村上第一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只是这一次貌似离最后一步最近。我想起村上的早年,他就读早稻田大学,逃学旷课,几乎无法毕业,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早稻田大学的杰出校友。这和他的文学路径有些类似,他喜欢卡佛、菲茨杰拉德等人,却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出了自己的作品,即使有通俗之嫌,但最终仍旧有可能获得殿堂的认可。我不想说村上的作品如何伟大,但是我觉得他最终得奖非常有可能,这或许也是给诺贝尔文学奖一次承认文学在真实世界影响力的突破。
手边有本村上作品集《碎片,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写于80年代早中期,那时候他最卖座的《挪威的森林》还没出版,他也在为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伤神,甚至会从早上写到三点过,烦得不得了了就去看电影。
《挪威的森林》电影海报
换言之,这本书是村上尚未大获成功之前的作品,从中可以一窥没有太多防卫心理的村上心声,有的话放在当下尤其值得玩味,比如他说这个“令人费解的世界”的名声和评价:“如果非要表达个人意见,我认为在这种信息过度密集的现代社会里,一切名声本质上都是过度评价。评价不足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被视为评价不足,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过度评价了。”
村上很喜欢菲茨杰拉德,也很喜欢国外杂志比如《君子》,二者也有联系。关于菲茨杰拉德下体的尺寸,因为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中的描写成为多年话题,以至于日后还有《君子》杂志创始人金里奇来澄清,尺寸“足够了”。村上看到这些新闻又无可奈何地感叹,作家这个行业不好混:“活着的时候要接受评论家恶毒的批评,死后连阴茎的尺寸还要被拿来大做文章。”
今天的村上不也是如此吗,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被批判,公布之后被揶揄,确实不好做啊。
本文节选自《不迷路,不东京》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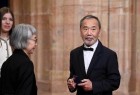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村上的小说有他独有的浪漫气息
2020-04-16 上午 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