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选译)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迄今所出长篇中唯一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上下卷加起来已热销430万册之多,甚至出现了“村上春树现象”“《挪威的森林》现象”这样的说法。一般认为,只要有一本书畅销,即可拓展作家日后的生存空间。而村上春树通过推出这部作品,以创记录形式实现了这一点。在国内,获得了以年轻一代为主的广大读者群,在海外也因《寻羊冒险记》英译本的出版而显露锋芒。《纽约时报》等各种传媒大加举荐,杂志《NewYorker》还刊登了其短篇《电视人》。应该说,这些都同该书创记录的畅销不无关系。
《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的开篇场面是颇为不可思议的:现年37岁大约身为作家的“我”乘坐的波音747即将降落在汉堡机场。但何以选在汉堡机场,飞机来自何处,则全然未予点明。一切都在降落于汉堡机场之际同过去的时间一刀两断,而被诱入再也无法返回原地的迷宫中,围绕“我”同“直子”往日回忆的故事即由此铺展开来。(中略)小说发行之初,作者自行设计的鲜艳的红绿两色封面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上卷使人想到血的红色代表生之世界,下卷使人想起苍郁森林的绿色象征死之世界。而两卷腰封颜色则完全相反。作者的想法似乎从这里也可看出:“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可是,作为死之世界的象征的森林的绿,却又是作为生之象征的女孩的名字——事实上很难这样一概而论。(中略)书中,阿美寮是“与外界隔绝的寂静的世界”。住在里边的直子是象征寂静的死亡世界的人物。而皮球般蹦蹦跳跳的绿子则浑身充满生命力。这种形成鲜明对照的两个世界交叉进行的方式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下简称《世》)中封闭与开放两个系统交错推进很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较之《世》将最初的疑念一直带到最后从而使人对高潮大打问号,《挪》则通过中间各种描写、插曲以及富有没、魅力人物的出场,而使各种疑念自然化解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例如“我”同绿子两次接吻即在绿子家晾衣台上和雨天在日本桥高岛屋天台上的接吻,“我”让奄奄一息的绿子父亲津津有味地吞食卷有海苔的黄瓜片那文静的身姿,尚不能同绿子交合的“我”往绿子内裤上一泻而出的情景;仿佛集享乐主义与纵欲主义于一身的永泽,非常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且打一手好桌球的初美,阿美寮中直子的室友、“我”与直子的知音玲子……这些场面和人物的出现,每次都一点点撩拔着读者。而这些有着微妙差异的震颤的叠积,在故事中逐渐形成共振,最后将读者卷入暴风骤雨之中。
如上所述,《挪》有很多地方可以同《萤》、同《世》加以比较。此外还有一部可以与之比较的作品,那就是《且听风吟》。(以下简称《风》)这部村上春树的处女作,同《挪》几乎是同一时代背景。两相比较,便不难看出村上春树在《风》中有意摈除什么,而在《挪》中有
意发掘什么。
在这两部作品中,作为有意摈除而又有意发掘的是性与死的问题。处女作《风》避开了性与真真切切的死,《挪》则积极地秉笔切入。也就是说,《风》与《挪》在性与死上面是互为表里的。除去直子,《挪》中还死了直子的姐姐,死了“我”的朋友木月,死了绿于的父母,死了永泽的恋人初美……死层出不穷,并且出场人物都很饶舌(以前作品很少如此),但在其妙趣横生倜傥脱俗的谈吐的背后,却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探索作为无言交流手段的性的问题。或者不如说,所有出场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是由各种各样的性与死之形式来维持的。《风》中说“鼠的小说有两个优点,首先是没有性场面,其次是没有一个人死。即使不理下睬,人也要死,也要同女人睡觉,天经地义”,拿这段话同《挪》里的场景相比较,便可看出村上春树已经走到了可以写性写死的地步,尽管他有着《风》的语言上的自觉。故事的最后,“我”终归未能向直子伸出援助之手,直子在阴森森的树林中自缢身亡。最终一个场面是“我”从电话亭里忘乎所以地打电话给绿子“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然而“我“无法回答绿子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发出的“你现在哪里”的问话,“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是在电话里连连呼唤绿子的名字,小说至此结束。
“哪里也不是的场所”这最后一个镜头,和这部长篇的第一个镜头同样给人留下一种难以释怀的感觉。读者很难单纯地认为“我”对直子的爱转变成了对绿子的爱——作者在有意阻止读者这样接受。因为降落在汉堡机场的37岁的“我”根本没有在回忆往事的第一章里提到绿于。“哪里也不是的场所”。“我”所抵达的场所不是选择冥界里的直子和生命力源泉般的绿子这两个恰成鲜明对比的世界的哪一
个,而是哪个都不选择又哪个都梦寐以求以致最后出现的终极场所。《挪》是以小说形式孜孜不倦地——不放弃任何一个——彻底发掘现代人这种生之希求的80年代代表作。
据日本《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村上春树Book》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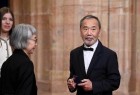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生与死(选译):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