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菁评《聽風的歌》
「村上春樹13部長篇小說巡禮專刊」 李維菁寫《聽風的歌》,轉自李維菁臉書
~~~~~~~~~~~~~~~~~~~~~~~~~~~~~~~~~~~~~~~~~~~~~~~~~~~~~~~~~~~~~~
村上春樹新作《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將出版,時報邀請,寫關於他的一本長篇小說。
題:呼吸,讓內在的風吹過
為什麼選《聽風的歌》?因為,這是村上叔的起點。
作為一個跟著他二十多年的讀者,我已經很習慣看著他在我前方跑步,他四十歲的、五十歲的背影,如今是他六十歲的背影了。我總是安心地向前望他,在小說的道路上,打著赤膊長跑的模樣。
後來我也開始跑,調呼吸,練身體。但是,這麼長的年歲過去,我習慣向前望著愈來愈成熟壯大的他,從沒想過回頭去看29歲的他。
剛開始的村上叔。
現在的村上叔,離當時的他很遠很遠了。
就連我,也老過當時的村上叔很多很多了。
一切都不同了。
現在的我再度翻開《聽風的歌》,他年輕模樣躍出紙面。那個多年前站在起跑點的模樣,那個落在時光那頭的他。
漩渦在我內部翻轉。
那個在日本文壇受到排擠爭議的青年,如今成為世界性的作家。我長期不肯讀他的任何評論,抗拒與人討論,彷彿這樣子他便始終是我心裡的秘密。
我看到餐廳打烊後,村上叔在夜裡廚房桌上寫字的畫面,那時他不知道寫作會引他走往哪裡,也不知道《聽風的歌》將開啟意外的人生。
如今回頭看《看聽風的歌》,我第一個反應是這小說寫得生。
特別是當這麼些年一路看到了《1q84》,突然回頭看《聽風的歌》,第一反應是生。另外,情感上的,則是時光的驚奇,現在的村上已不是徬徨青年,書內那份純真的哀傷年輕得令人心痛。
那時候他想寫,卻不知道寫不寫得出來?他想寫,又反覆質疑寫作是什麼?文學與生活的關連是什麼?生活表層凝結那層灰濛濛的虛無,是視線的誤差?那層看似髒污的粒子有天會因時光之翼的包裹而結晶閃耀?那垂直毫無漸層的黑暗是什麼?是惡或者只是回憶?
以及,那些東西為什麼盤繞不去,總是回頭找你?
那個時候他還生,卻也無與倫比的誠懇勇敢。
而他那些反覆質疑,困惑悲傷,也正是我懷有的。
「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就像完美的絕望並不存在。」
「寫文章並不是自我療養的手段,而只不過是對自我療養所做的微小嘗試而已。但是,要說的坦白真誠,卻非常困難,我越想說實話,正確的語言就越沉到黑暗深處去。」
我一直反對村上叔早期作品被貼上青春傷逝或都會感受性這樣的標籤,無疑他當時揭示出一個嶄新、時代性的語言風格,因此引起這樣評論;但我認為這樣的評論,就像聽一個人說話,只看說話的語氣,卻沒好好檢視說話的內容。
不過,世人多如此:看態度,看語氣,看外表,用此判定。也因此,有的人說話,老強調自己嚴肅雄壯,正氣激昂,甚至用力奮命,汗流浹背;人們見那說話的人滿身是汗、氣喘如哮,也就認定此人之言必然嚴肅經綸。村上不是這樣的,再深刻、再傷痛、再凜然、再陰暗、再泫然欲淚、再與體制逆反的,他都用一種不經意、不亢不卑的口吻說。人們著迷於他的口吻,卻忘了他看似輕快吐出的東西,其實建構在對生命極度的認真之上。
嚴肅的事,他用輕便的口吻說;比起那些用嚴肅口吻說平庸話的,高貴多了。
如果你也曾仔細看《聽風的歌》,便知道29歲的他多麼不放過自己。
當然,那麼直白地挖出自己內臟,當村上叔的小說語言愈來愈熟後,便不用這種方式對世界提問了。相反的,後來的讀者可能抱怨,他小說寫得像一個充滿問號的游泳池。
但這個晚上,當我再度進入《聽風的歌》,感受複雜,震動隨著理解升起。
啊,他始終是那個他哪!那個29歲的青年,始終在四十歲、五十歲以及六十歲的他的體內。
《聽風的歌》,後來的村上其實全在裡頭。
地下生出橫向通道的井、受過去囚禁有自毀傾向的女孩、充滿救贖能力的精靈少女、中國人….等,這些在《聽風的歌》便出場的人物、線索與原型,後來一而再再地以不同程度、不同分量的變形,反覆出現往後三十年的作品中。還有,《聽風的歌》登場的雙胞胎,以及雙胞胎折射出的雙重自我、雙重世界、迷宮般與現實對映的超現實世界,在他日後的小說中,以角色、以意象、以情節、以結構,再三演練。
《挪威的森林》、《尋羊冒險記》、《發條鳥年代紀》、《舞舞舞》、《國境之南太陽之西》、《世界末日冷酷異境》、《海邊的卡夫卡》以及《1Q84》,當你認真檢視,他每部小說的密碼,都藏在這部原點之作。
一切早在當年便埋伏了。
某種意義上,這代表村上叔從沒忘記年輕的疑惑,不曾背棄純真的質疑,沒忘記對文學反覆拷問,他在時光中以小說找尋答案,只是形式一變再變,語言精熟又轉圜,而他還是原來的他。
我都要老過他了,突然意識到,那個對世界充滿相同疑惑的青年,三十多來始終都在;而我心中那股深恐遭到遺棄的不安,老想拋棄過往卻又絆跤的難堪,竟被這位文學家人深深撫慰了。
「雖然如此,寫文章也是一件快樂的事,因為比起活著本身的困難來看,為它們加上意義,是太簡單不過了。」
我深信真正的作家,自始就明白,文學不能當作霸凌世界的最崇高價值,比文學更上頭的,是活著本身的困難。
不管生、不管熟,他始終是他,村上叔。
就像你看慣60歲的鍾情之人,有天突然拿到他29歲的照片,第一眼是「天哪,變化真大」對時光刻痕的訝異,第二眼卻明白,照片裡的他,眉眼、嘴唇、下巴的線條,還有那份神氣,其實沒變。
他還是原來的他。淚潸潸之後我也願意相信,我還是原來的我。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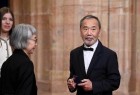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李維菁评《聽風的歌》: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