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蓝调——读村上春树
认识村上,是因为那本《海边的卡夫卡》。一次运动会上,对任何体育项目都不擅长的我百无聊赖,于是从同学那里借来这本书。封面是浅浅的白和淡淡的蓝,下方的沙滩上留着一个少年的影子,显得空灵而寂静,似乎有什么从这样的画面当中散发出来,弥漫于空气。我就打开来看了下去。开始时平淡无奇,但是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就被某种奇异的魔力所吸引,一直读下去,直到把它读完。
这本书充满了少年时代海一样的迷惘和忧伤,如同一个淡蓝色的梦境让人沉湎其中。我就从那时开始走进了村上的世界,那片和海洋一样变幻莫测又充满魅力的世界。我想每个人都是一片海,即使从小生活在山区的人,在潜意识里也一定有着对海风和海水的向往。而我幸运地走进的这片海,这片村上的海洋,风景这边独好。
潮润的海风
讲到海,就一定要说到海风。对于村上这片海而言,这风往往是轻柔的,带着点抚摩的意味。然而这风却决不是隔靴搔痒地一吹了事,它在吹过你的同时,也把来自海洋的水气带进了你的心扉。
这风是什么样的呢?先来看一段村上的文字吧。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载沧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轻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10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仿佛冻僵似的紧贴着湛蓝的天壁。凝眸远望,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拂过草地,微微卷起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木从中蓦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挪威的森林》
很美的风光,如田园牧歌般天然清醇,还有一个美丽的女孩陪伴左右,此情此景,该是很令人向往的吧?然而不,“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的”。这看似不经意的句子就好象风里夹着的一粒盐,在你甚至没有察觉的时候飞进你的眼睛,同时给你的心灵一次轻而有力的叩击。
而当我们读到小说结尾,直子自缢身亡,主人公一个人在沼泽般的寂寞中摸索人生的时候,海风就吹来了一片雨云,你即使不流泪,也要惆怅许久。在那个看起来光鲜亮丽而实际上虚假乏味的社会里,三个主人公艰难地挣扎着,而这挣扎的全部目的仅仅是捍卫生命中平凡的美好,但等待他们的结果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幻灭。这时候,海风仍然轻轻吹过,但它已经吹入你的脑海,使你回味,使你深思。
很多时候,村上小说中的描写和对话就像樱花,以似乎漫不经心的姿态飘落,那满地的落红却是动人的凄美。“于无声处见真情”,大抵也是如此吧。
原地打转的旋涡
不记得是谁说过,要获得阅读的快感,最好去读一个作家的长篇小说;要是你想在最短时间里抓住一个作家的灵魂,那么去看他的短篇小说集。
村上的短篇我也看了不少,最近在翻的两本是《电视人》和《旋转木马鏖战记》。
“越是倾听别人的讲述,越是通过其讲述来窥看每个人的生态,我们越是为某种无奈所俘获。沉渣即是这无奈之感,其本质便是我们哪里也到达不了。我们固然拥有可以将我们自身嵌入其中的我们的人生这一运行系统,但这一系统同时也规定了我们自身。这同旋转木马极其相似,无非以同一速度在同一地方兜圈子而已。哪里也到达不了,既下不来又换不成。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被谁超过。然而我们又在这旋转木马上针对假设的敌手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鏖战。”
——《旋转木马鏖战记.序言》
这就是村上对于人生的观点(也可以说是部分的观点),人生就好象旋转木马的游戏,无论你怎么努力,曲终人散时不过回到原地——然而我们不能不这样,因为中途下场就意味着死亡。
你可以说他悲观,可是你必须承认,这样的人生观在某些条件下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村上所描写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被挤压成罐头那样的东西,变形的同时索然寡味,所有人的生活都遵循着既定的轨道,看似繁华热闹,其实都在原地打转,哪里也到达不了,相反身处其间的人们感到越来越空虚无聊。就像大海上那些凶险的旋涡,不但原地打转,还会把来往的大小船只统统拉来殉葬。
作为短篇小说,村上的这个集子丝毫没有日文小说粘乎乎的通病;相反,遣词用句干净利落,笔锋犀利,颇有点鲁迅的味道。
“他有一项少见的本事,能长期一天不缺地坚持写日记——这样的人是为数不多的——因此能够查出呕吐开始与结束的准确日期。他的呕吐始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晴),结束于同年七月十五日(阴)。”
——《呕吐一九七九》
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突然患上神经性呕吐,同时不断接到奇怪的骚扰电话,只要一接电话就必然呕吐不止。非常匪夷所思的故事,结局也非常离奇——四十天后症状自行消失,此后再没发作,生活就像旋转木马一样回到了原来轨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此人生活中很有规律的一项内容,就是放着找女朋友的机会不要而去和朋友的妻子睡觉,长此以往,直到接到奇怪电话,呕吐不止的那天。
究竟是什么原因呕吐,作者没有明说。但是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呕吐也好不断记日记也好和朋友的妻子睡觉也好,都是生活的一种病态。在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像是一台机器的某个零部件,个人的价值很难得到承认,甚至少了自己这台机器照常运转。于是,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就以千奇百怪的方式,甚至极其不正常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样的方式有作用吗?看看作者的文字就知道,不过是自欺欺人,在旋转木马上你死我活地鏖战一圈,临了照样回到原点。
有办法消除这些生活中的旋涡吗?你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村上,他也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你——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只好和他们一样原地打转,而他原地打转的方式就是写小说。至于怎么走出这个怪圈,自己不努力,怕是一辈子也明白不了!
铺天盖地的海啸
“当然,实际上你会从中穿过,穿过猛烈的沙尘暴,穿过形而上的、象征性的沙尘暴。但是,它既是形而上的、象征性的,同时又将如千万把剃须刀锋利地割裂你的血肉之躯。不知有多少人曾在那里流血,你本身也会流血。温暖的鲜红的血。你将双手接血。那既是你的血,又是别人的血。
而沙尘暴偃旗息鼓之时,你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何从中穿过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已经远去你大概都无从判断。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含义。
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离开家,去远方陌生的城市,在一座小图书馆的角落里求生。”
——《海边的卡夫卡》
这段文字依旧波澜不惊。然而仔细品味,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涌此起彼伏,一场海啸正蓄势待发。
“叫乌鸦的少年这回把尖嘴啄进对方讲话的嘴里。一对大翅膀仍然急剧地扑楞着,好几根黑亮黑亮的羽毛脱落下来,如魂灵的残片在空中盘旋。叫乌鸦的少年啄裂男子的舌头,啄出洞来,拼出全身力气用嘴尖把它拖到外面。舌头极粗极长,拖出喉咙后仍像软体动物一样叽哩咕噜爬来滚去,聚敛着黑暗的话语。没了舌头的男子到底笑不出了,连呼吸都好像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声地捧腹大笑。叫乌鸦的少年细听其不成声的笑声。不吉祥的空洞的笑声如掠过远方沙漠的风一般来说永无止息,未尝不像是另一世界传来的笛声。”
——同上
上面的文字着实触目惊心,我们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把这个世界毁灭再重新构造的伟大而又令人生畏的力量,如同刚刚在东南亚发生的大海啸,巨浪起处,一切荡然无存,而晨曦一现,希望又回到人间。
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村上53岁,53岁还能有如此的勇气和激情向命运乃至整个世界发动进攻,实在让我们钦佩。看来村上的海洋注定不是永远风平浪静的,他可以用尽生命的力量掀起一场海啸席卷我们的心灵,因为天性热爱自由的他和我们一样不甘于在旋转木马上做成人游戏,他一样渴望变革和新生。
所以我很反对简单地把村上归为小资,他显然要有勇气得多,也有内涵得多。有些人仅仅为了获得一个“小资”的虚名而去读他的书,不但是对他作品的亵渎,也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这就是村上,像大海一样富有张力和文采,像大海一样拥有最真诚质朴的性情。无论阴晴我都愿走进这片海洋,去感受它的博大和凶险,同时尽我所能,把一片海带到另一片海。
(完)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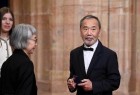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海的蓝调——读村上春树: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