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投稿 | 我们的文学遗产 ——从托尔斯泰和陀氏再到库切和村上春树
2014-02-26 孙永登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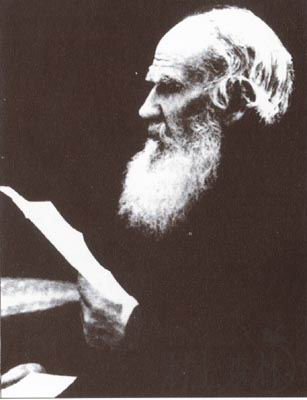
我们的文学遗产
——从托尔斯泰和陀氏再到库切和村上春树
文/孙永登
刚刚过去的这个年头是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从波利亚纳秘密出走(今属俄罗斯联邦梁赞省),和妻子以及自己受惠终身的农奴制彻底决裂,10天后病逝在一个小车站。此前,他多次从自己380公顷的封地出走,多次对自己的博爱思想产生怀疑,多次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度,并被东正教除名(东正教历史上,只有四个人遭到开除教籍)。
从历史向前回望,1869年十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侨居的德国小城德累斯顿回到俄国,去找寻死去的幼子巴维尔生前生活的踪迹。他负债累累,苍老孤独,这段苦涩的回忆后来变形为小说《群魔》。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南非人J·M·库切将这段还乡历程加工成一部伟大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与库切200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耻》相比,这部作品更加贴近人心和世界,更加主题淡化,因此更加复杂多义。

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日本人村上春树作了著名的“鸡蛋和高墙”的演讲,提出了“体制化杀人”的概念,算是对上述历史遗产做了现代化清算。
在新作《1Q84》中,村上春树对遥远的乔治·奥威尔致敬。其实,不只是奥威尔,《1Q84》的隐喻还可追溯到一位犹太人——卡夫卡——身上。进不去的城堡和无所遁形的高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我国,它有一个专门称谓:有关部门(关于监狱和专制,可参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一圈》和余华《往事与刑罚》)。
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这样的论述:“这两位作家是对立的,托尔斯泰是史诗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陀氏是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戏剧气质的人;托尔斯泰沉迷于理性和事实,陀氏蔑视理性主义,热爱悖论;托尔斯泰像一个站立在大地上的巨人,唤起真实可见的整体具体经验,陀氏总是处于幻觉的边缘;托尔斯泰历史性地在时间的河流中看到人类的命运,陀氏从戏剧性暂时的静止状态观看人类”。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另有高论:“生命支配着托尔斯泰,就像灵魂支配着陀氏”。
这是他者眼中的不同,由此差异构筑了文学现象的纷繁场景,但共性是什么?或者说,造成作品打动人心的共同心理基调是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与前一个时代相比更加技术化,利益格局更加多元,“美国无处不在”(赫鲁晓夫的孙女在华盛顿大学发表的演说辞);然后,人的生存更加没有质感,如果把路牌标识去掉,你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见到的银行LOGO和东京并无不同,苏州工业园的博世电动,三星电子,爱默生医疗直接拉平了洲际概念,但物质躯壳变化下的精神元素,或者说:人——的内核——有无变化?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封地给农奴造房子,自己做鞋子,1859年左右给庄园附近的农民子弟办了二十余所学校。但晚年,他对自己曾经身处的“知识阶层”立场深感怀疑;作为比较的是,在《彼得堡的大师》中,库切也让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早年赞同的涅卡耶夫式的极端革命开始怀疑,从而重回“弥赛亚情结”。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本源恶”深恶痛绝,但他走不出自己的时代,他只能走出自己的封地,在冰天雪地里自我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没有太大的信心,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经常长着两幅脸孔,自己和自己对话,巴赫金称之为“复调”。他自己建构了一堵墙,如果说,宗教是其救赎的通道,是拯救灵魂的最后一束光,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亲手将他堵上了。在中国,北村可以说是陀氏理论的继承者,他的《施洗的河》《公民凯恩》是俄罗斯声音的福建翻版,连最后的释放通道都一样:基督教。问题在于:中国素无宗教信仰传统,或者说,作为一个东亚民族,中国人从来不是善恶二元对立的民族(姜文《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小说,在电影叙事里,中国人可以和日本人在村子里唱大戏,直到对方露出枪口)。
贯穿在上述四者将近一个世纪递延下来的精神谱系是:他们笔下转动的世界不是来自伤感或者自我陶醉式的修辞把玩,而来自关照,来自对世界的谴责,来自对人类疾病的疗救方法的寻找。他们眼中的冲突有两种:人和国家的冲突,人类愿望和社会必然的冲突。他们笔下的“人”在代替整个人类受难,他们对自身充满了怀疑和自诘,他们从“知识阶层”的既有立场出发,自觉的加入到底层人群,去感受他们的寒冷,以及造成寒冷的决定性力量:体制。
如果说,村上春树的逻辑立场是:
物语(小说)——体制(多数暴政)——小说家
那么,从托尔斯泰和陀氏再到库切再到整个知识阶层的逻辑立场应该是:
学问——体制——知识分子(知识阶层)
他们用小说这种媒体介入生存,自觉肩负了用历史责任感去解读和对抗国家暴力性的任务。从叙事本身跳出来,他们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本提供者,而是一个对生存的发难人:为什么活着,以及怎样活着?

村上春树对体制做了如下论断:“人一旦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从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听命于教旨及其原则,因为这样活的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在日本人的概念里,没有善与恶这类二元概念,或者说,这类概念的界限不明晰,他们的个体如果说存在着模糊的对立概念,那么整体代替个体的体制本身则没有,就像菊花与刀都是他们的象征一样。体制一旦形成就可以自发转动,衍生出自我意志,这类整体意志代替了个体意志,也成为个体脱罪的遁词。因此,靖国神社的参拜者不被日本人视为一个个人,是体制自己发出的声音。日本的近邻朝鲜也相似,金日成的思想可以替代四千多万公民思考,可以将公民依据法律划分为四十一类职业,体制将之称之为:“主体思想”(主体思想无限大,类似于道家所说的“气”)。
在这里,我更愿意将“体制”解读为一个泛化概念。就是说:它既指“9.11”的伊斯兰分子,也指把美军个体派到伊拉克作战的国家机器;它既指让山西大同和河南渑州的矿工失去生命也失去数字记录的神秘力量,也指让等同于欧洲大陆的人口在短期内完成“春运”的计划调配手段;它既指造成每年半数高等教育毕业生失业的教育机制,也指世界上最大的团体操“阿里郎”;它既指暴力拆迁,跨省追捕,也指高铁速度下的骇人票价。
一旦听凭以美好动听的名号出现的“善”大行其道,难免会出现例如“大清洗”和战争,难免会出现沉默的大多数不能发言,难免会出现让CBD的光鲜把底层“蜗居”和“蚁居”遮蔽掉的话语暴政。
因此,小说家的身份其实不是这一个世纪的全部遗产,上述四者对这个世界的馈赠在于:勇气,良知,担当意识和内省精神。这是他们和他们笔下的生存代言人的内在逻辑联系。
也因此,我们可以从文本和文学里跳出来。所有符合以上特质的知识阶层或者非知识阶层共同体我们都可以给他们命名: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共同体范围很广:从草婴到杨宪益,从茅于轼到蔡定剑,从郑永年到周兼明,从韩寒到《南方周末》……只要符合以上特质,只要他们的立场仍然是:“人”——具体的微小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实践这个遗产(而不必追究他们是否有“索绪尔”这类名词指称作为外在符号)。
而相对的,一些打着知识分子(“知道分子”?)标签,有学历(或者说:有文凭),以会英文为荣(托尔斯泰的时代是以会法文为荣,这也算是与时俱进),内心完美,技术纯熟的将学问和知识脱离开的“知识拥有者”,其实已经与这个传统渐行渐远,比如,作出“上访者99%都是精神病”论断的北京大学某教授。
诚如晚年巴金先生所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的作者赫尔岑所述:“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就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的肩膀,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制度。”;按照福柯的说法,知识本身即是一种权利。
知识阶层如果不对自己的立场和责任时刻保持清醒的审视,就会放弃所有的文化遗产,就会运用话语权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为体制和暴力背书,就会产生大量的“车延高体”和词语自我内循环,就会脱离大地和苦难,就会把文学的精神抽空。
参考文献:
舒可文.托尔斯泰:向聋子提问的人 [J].三联生活周刊,2010,47:70
薛崴.托尔斯泰的三部小说 [J].三联生活周刊,2010,47:62
林少华.《1Q84》:当代“罗生门”及其意义[J].外国文学评论,2010,2:111-123
一稿急就于 2010年冬 江苏苏州
修改于 2014年春 江苏常州
————————————————————
分享朋友
点击右上角按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分享朋友圈”。
关注帐号
在“查找公众号”中搜索“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或“CSCS208209”。
昨日文章
点击“阅读原文”可看到昨日分享的一篇文章——《迷茫的森林,迷失的我》。
文 艺 连 萌——物 质 时 代 的 修 行 者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原创投稿 | 我们的文学遗产 ——从托尔斯泰和陀氏再到库切和村上春树: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