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眼中的村上春树
美國哈佛教授傑‧魯賓(Jay Rubin)寫了一本關於村上春樹研究的專著:《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哈維爾出版社出版)。魯賓在哈佛專門講授和研究日本文學,著有《妨害風化:明治時代的文人》(Injurious to Public Morals: Writers and the Meiji State"),翻譯了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發條鳥年代記》、《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以及夏目漱石的兩部小說。
當然,以我貧瘠的英語水平不可能完全領會英文原著,我讀的是臺灣中國時報周月英女士用 E-mail 傳來的二校電子譯稿。儘管案頭瑣事成堆,但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這是因為,一來我原本也想寫這為一部帶有評傳性質的村上研究專著,卻因忙於村上文集的翻譯等原因遲遲未能動筆,現在看到別人搶先一步,自然急於看個究竟;二來這部書的確寫得不錯。老實說,我看過不少日本學者寫的關於村上研究的論文和專著,但總覺得不夠到位,甚至不得要領──他們太拘泥於細節了──而魯賓則從大處落墨,線條奔放,一氣流注,頗有高屋建瓴之感。讓人覺得哈佛終究是哈佛。
魯賓原先從事以夏目漱石為主的日本近代文學研究,1993 年開始研究村上春樹。村上在美國時曾同村上比鄰而居,在大學課堂上同村上一起討論過日本文學,聽了村上在美國直接用英語做的講演,加之是村上部分作品的譯者且是村上書迷,從事村上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此次他融會貫通村上迄今刊行的幾乎所有作品和訪談文章,抽絲剝繭,條分縷析,從中梳理出這部《村上春樹傳》或《村上作品傳》。關於撰寫動機,他在〈致讀者〉中說,一是解答他翻譯村上作品後讀者向他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為讀者提供一些未見於英文的背景資料;二是以其個人的學術經驗閘明他對「村上的感受,包括指出其創作上的不足」。
魯賓列舉了在日本對村上批評較多的主要人物:西方的日本文學研究泰斗唐納德‧金(Donald Keene)、大江健三郎和三好將夫。三好將夫甚至認為村上是個玩世不恭的寫手,沒有任何詞句出自靈感或內在衝動這一傳統創作動機,要人們不要太認真看待村上──「只有極少數人才會笨到用力讀他的東西」。魯賓於是寫道:「好吧,那就讓我們當一回笨蛋吧!」不用說,哈佛教授一般不至於是笨蛋。他眼中的村上既不完全是日本人眼中的村上,又不等同于我們中國人眼中的村上,只能是一個美國教授、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村上。這樣的村上是怎樣的村上呢?下面就讓我簡單概括並品評一下這本專著中的主打觀點。
其一,魯賓認為「尋找」是村上作品的核心。談到村上作品的核心時,魯賓有兩個不同表述,一是「自我和他人之間彼此瞭解和誤解的程度,逐漸成為他作品的核心」。二是以《1973 年的彈珠玩具》為例,認為尋找能同 208 和 209(以及「某一天俘虜我們的心」的什麼)「再會」的某個地方「是村上春樹的創作核心」。談得較多的則是後者。在《1973 年的彈珠玩具》中尋找三年前消失的彈子球臺,在《尋羊冒險記》尋找那只帶有星形斑紋的羊,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中尋找人類心智和它所認知的世界之間的關聯,在《發條鳥年代記》中尋找丟失的貓和離家出走的妻,幾乎在所有的作品中「尋找認同,以及愛的意義」……。應該說,魯賓這個見解是中肯的。2001 年 9 月村上應筆者之請以《遠遊的房間》為題致中國讀者的信中明確寫道:「我的小說想要訴說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簡單概括一下。那便是:任何人在一生當中都在尋找一個寶貴的東西。但能夠找到的人並不多。即使幸運地找到了,實際找到的東西卻已受到致命的損毀。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繼續尋找不止。因為若不這樣做,生之意義本身便不復存在。」
不過,村上不會無趣──魯賓指出──他的尋找過程,「全部以喜聞樂見的輕鬆形式處理,不沈悶滯重,不抑鬱,誠懇而全無為善的幻覺。他用我們這個時代的語言向我們描述極度虛無的、令人敏感的生活的真正趣味和躁動。」若允許我冒昧補充一點,除了尋找,還有消失。因為消失才尋找,或者說因為要尋找才消失。消失與尋找,可謂村上文學的核心或一大主題。
耐人尋味的是,對於我們中國人閱讀村上時一再感受和沈浸其中的孤獨、寂寞、悵惘等所謂小資情懷,這位美國人、美國學者幾乎只字未提──僅偶爾使用「失落」、「空虛」等字眼──並自信地斷言: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在東亞除日本以外的國家賣得特別好,是因為「書中冷靜疏離和經常帶有戲謔語氣的為事者似乎為生活在儒家嚴厲宗族制度下的讀者提供了另一種出口」。這個看法就未免有點越俎代庖了。從書上看,至少他對村上作品在中國大陸的發行和閱讀情況並不清楚,所舉例子是臺灣和韓國的。殊不知,中國的宗族制度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被毛澤東踢到爪哇國去了。
其二,魯賓認為村上作品的文體特色可以歸結為三點──簡約、韻律、幽默。當然,這並非魯賓的獨家之言。難得的是他提供了村上本人的表述並進一步加以分析和印證。例如他引用了村上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英文講演(這是一般日文資料中所沒有的):「我的風格總的說來是這樣:首先,我只在句子裏放進真正必要的意義,絕不多放;其次,句子必須有韻律。這是我從音樂、尤其爵士樂學來的。」這裏,「絕不多放」可以理解為簡約。而關於簡約,村上說他是從馮尼格特(Kurt Vonnegut)和布羅提根(Richard Brautigan)的作品中學得的。不過,就村上的處女作《聽風的歌》來說,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他沒有時間寫和長句子,那時他正在熱火朝天地開酒吧。關於幽默,這是每個讀者都可以感覺到的文體特點。魯賓進一步引用村上本人在美國說的話,除了簡約和韻律,「我想擁有的第三種風格是幽默。我希望別人可以開懷大笑,希望他們能不寒而慄或怦然心動。我的作品應該具有這樣的力量,這對我很重要。」不過魯賓認為,儘管幽默是村上小說得以跨越種族藩籬的重要元素,但最重要的則是「村上能夠控制你的思緒、激發各種不可思議的意念」。這點總結得很妙,相信我們中國讀者也會有同樣感受。至於中國讀者感覺到的行文的優美,魯賓則從未提及。我認為這裏面至少應有兩個原因:一是世界上大約鮮有像我們這樣對詞章之美敏感的民族;二是世界上大約少見像漢語這為講究裝飾美的語種,儘管原則上任何語種都有對等交換價值。作為譯者,有一點讓魯賓感到惱火:使得村上小說顯得清新可喜的英文味兒,在翻譯「回」英文時恰恰成了「流失的那個部分」。
其三、魯賓特別強調了村上小說中的「距離」。村上在《聽風的歌》中借虛擬作家哈特費爾德之口說道:「從事寫文章這一作業,首先要確認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間的距離,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魯賓認為,這個實驗日後成了村上──村上是個認識論者──所有創作活動的基礎。不僅村上和他筆下的文字之間有距離(村上解釋說那是因為他極想寫作,卻又沒什為好寫的),而且村上和他設計的故事情節之間也有距離,謹慎地控制細節與結構,情節的推進疾馳有度,「如同向朋友訴說他的親身經歷。二十年來,村上一貫運用友善可親『我』作為為事者,這已成為他為事策略的重點。……可以說,村上以『我』為為事者的作品中,唯一的『人格』就在『我』身上。他的觀點不斷散發魅力,其他角色只是他精神影響下的配件。村上的故事焦點經常在於『我』奇特的觀點或遭遇(這類場景比比皆是),而不在廣泛的性格探索或緊湊情節的鋪展。」魯賓還認為村上的冷漠和距離還表現在對待生命的態度上,好在沒有荒涼感,讀起來較為輕鬆,猶如粉彩世界,偶爾透出幾許傷感。魯賓進一步斷定:「平凡和親切是他作品最顯眼的特徵。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體察出了市井小民的生活中的玄秘和疏離。」
應該說,魯賓這些見解是很讓人信服的,儘管前後有時不夠統一(原文基本以作品為序,沒有統一概括性章節)。筆者也曾嘗試就此加以梳理──除上面的以外,我覺得村上的距離感似乎還表現在他對社會制度、對官僚機構以至他置身其間的現代都市的無視和揶揄,從而守住了自己的靈魂制高點和精神優勢。
其四、魯賓在大力強調村上作品的特殊風格即如何有別于日本其他作家之餘,也提到了二者的相通之處。例如一般認為村上同以表現「日本美」為依歸的川端康成和注重社會性和知識份子使命感的大江健三郎大相逕庭。但魯賓卻敏銳地嗅出村上同川端之間相同的氣味:「兩人在作品中都試圖捕捉無情帶走生命的時間河流,並以淡漠作為解脫之道。」關於村上同大江,魯賓認為這兩位作家都致力於追問和驗證歷史與記憶、傳奇與故事等問題,都不斷深入情感的黑暗叢林,探索他們個人及其身為世界公民和日本人的真正身份。同時指出村上小說同樣具有日本小說特有的傾向:簡短、各自成篇。因為除了《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村上的長篇通常是許多小故事的組合,沒有龐大的整體結構。「它們始終令人目瞪口呆、大吃一驚,娛樂性十足又具有為示性。」
不過魯賓作為西方人,難免對另一個相同之處有所忽略──無論村上的小說帶有多為明顯的西方文學印記,但其骨子裏、其意識和情致的深處,仍浸透著日本根深蒂固的「無常觀」。這種「無常觀」使得日本人分外關注萬象變化的神奇微妙、個體生命的稍縱即逝以及宇宙間無可捉磨而又可能有所感應的玄機和偶然性。村上小說中的孤獨、無奈和達觀情境在根本上是與此一脈相承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點──魯賓特別提到村上對中國及中國人的態度。村上的父親戰前是京都大學的優秀生,在校期間被徵召入伍。村上小時聽父親講過在中國的駭人經歷。此後他「對中國及中國人的情感便十分矛盾」。魯賓就此詳細分析了《開往中國的慢船》這個短篇(去年見面時村上向筆者強調此篇是依據他的親身經歷寫成的),從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接觸的幾個中國人心懷歉疚,「看出村上的確持續地對中國反思,同時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是日本人的一段痛苦回憶。」
可貴的是,村上沒有至此止步,他還把筆鋒指向日本這個國家最黑暗的部位。魯賓分析道,在《尋羊冒險記》中村上認為是「先生」那樣的邪惡力量和權威主義傳統「致使日本政府殺害無數中國人」。《發條鳥年代記》最後一段出現「猶如一把中國刀」的尖銳的上弦月,而此時「中國代表著日本軍隊在戰場上犯下的駭人屠殺惡行」。村上在美國創作這部長篇的第三部期間,一次接受採訪被問及「為什為你們這一代人要對自己出生前即已結束的戰爭背負責任」,村上回答:「因為我們是日本人。當我從某些書上讀到日本在中國的暴行時,簡直不敢相信。……我想知道是什為驅使他們做這種事,去殺死或傷害數不清的人們。」並且斷言「暴力是理解日本的關鍵」。
筆者也對此做過一些研究。應該說,從《發條鳥年代記》開始,村上開始告別「淡漠」和「距離」,轉而擁抱責任,尤其對日本漸漸懷有社會責任感,其中最主要的是開始質疑那段不少日本人諱莫如深的歷史。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天的日本社會儘管戰後進行了許許多多重建,但本質上絲毫沒有改變。歸根結底,日本最大的問題點在於:戰爭結束後未能將那場戰爭劈頭蓋腦的暴力相對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現,以非常曖昧的措詞改口聲稱『再不重復那樣的錯誤了』,而沒有人對那架暴力機器承擔內在責任,沒有認真地接受過去。」坦率地說,能夠對那段歷史採取如此態度的日本作家是極為罕見的。在這個意義上,村上絕不僅僅是執著於個人主義的或所謂「後現代」作家,同時也是敢於追問一般日本作家不願或不敢追問重大歷史事件及其意義的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作為中國讀者,更應對此、對這個日本作家的勇氣和良知給予充分的關注和評價。在閱讀魯賓這部專著當中,筆者對此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和更多的思考。
順便說一句,魯賓這部專著上海譯文出版社已經引進,現已翻譯過半。臺灣繁體字版(周月英譯)將於近日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文中引文即來自臺灣二校後的電子譯稿,引用時對個別詞做了技術性改動,在此一併致以歉意和謝意。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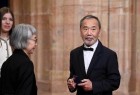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哈佛教授眼中的村上春树: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