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村上春树
一个是对民俗趣味怀有强烈好奇的学究型少女,一个是游荡酒吧的浮滑少年,张爱玲和村上春树,似乎形象和作品从哪一方面来说都绝不相同,可说是就算碰了面也不会跟对方讲话,就算是在正午最拥挤的餐馆里也不可能并桌喝茶的两种人。如果要他们并桌,至少得把两人之间的距离对折九十九次才行。地球跟月球的距离如果折叠这么多次,大概也早就对撞在一起了。
唯一可能的是,在作品中互相嘲笑对方。张爱玲喜欢嘲笑自认诚恳的无能男子,村上春树喜欢嘲笑问太多说太多爱太多的犯错女人,尽是一些有骂到对方嫌疑的事。这可能是他们唯有的两种互动之一。
另一种则是他们共同从事于譬喻的事业。所做的事和广告文案作者、编辑、法官与擅取绰号的小学同学一样,是为世上无数随便取了个名字充数的事物重新命名。广告人替桌子和椅子分别拟制感人的标题;法官在罪行当中寻求其本质,而以唤出它的名字使其失去魔力;坏孩子则透过小学生对电视节目共有的广博知识,用一个角色的名字把导师推入某出八点档的幻境情节里,万劫不复无可脱身。任何一种命名的事业均有其特殊的处理方法,共通点是均属于有系统的扭曲。
张爱玲的众多修辞系统下面又有很多次系统,这些与其说是字词选择,不如说是某种人格,例如可口可乐情结。可口可乐瓶身的原始灵感来自设计者女友穿著时髦窄裙的身形,这件事在张爱玲身上则以瓶子和女人、衣着的无限上纲联想出之。《倾城之恋》女主角穿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支瓶」、「药瓶」。而对于男主角,「妳就是医我的药」。「连环套」的霓喜在外人眼中则是「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
以村上春树来举例的话,最著名的次系统该是动物的臆病症候。这是一种把任何生理的不适、力不从心归罪于某些没有见过面的动物的倾向。《寻羊的冒险》里老鼠说「对年月的感觉渐渐迟钝起来,彷佛有只黑鸟在头顶上嗒哒嗒哒地振翅,使我无法数算三以上的数字。」「我的缺憾随着年纪愈变愈大,即是体内养着一只鸡似的。鸡生蛋,蛋又变成鸡,那只鸡又生蛋。」(博益版)取代鸟类的,是《梦中见》和《舞.舞.舞》对灵长类的敌意:「朦胧中,一只巨大的灰色猿猴,手执槌子在我的脑后狠狠地一击,我昏睡过去。」(故乡版)
重新命名的效果可能是精确化,也可能反而变模糊了。总之就是使人产生某些固定联想的强迫性思考。就如逛街时遇见夏天,会想到「夏一跳」「惊奇一夏」之类的用语,读者也会不断地在女性身上遇见张爱玲的瓶瓶罐罐们,或是偶尔直觉想找鹪鹩为头痛负责。不仅是譬喻的成品,以小说碎片的形式嵌入读者日常感官,连他们技术的手腕都会在此陵夷相争。生活中某人绽现的譬喻,就像是在张爱玲可乐队,或村上春树宠物队的计分板上又加了一分。这是在两人所不知情的彼此谩骂之外的,两人所不知情的票房斗争。
《 挪威的森林》里有一口井,在荒郊野外。据渡边回忆,这口水井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它那直径约一米的黑洞洞的井口不动声色地掩藏在青草下,井口四周既无栅栏,也无石楞,便连石砌的井围,经过大自然的洗礼,也已裂缝纵横,只落得为绿色小蜥蝎提供了绝好的嬉戏场所。井筒非常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了里边”。就是这样一口井,很深,很危险,每三年两载就有人准保掉进去。
渡边怀疑是直子的臆造,世上本没有这口井。然而它掩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不止直子,不管你否意识到,等时机一成熟,它便让所有的黑一起出动,或者仅仅释放一两种出来,或一下拽你下去,或慢慢诱你入井。木月首当其冲,他那么开朗、活跃,诱惑他的黑是什么,是对于死亡的好奇?或者长期积聚下来的不愿为人知的成长的烦恼?他竟然自己一下子跳了进去。永泽英俊潇洒又聪明,家里也有钱,但他很孤单,从他的井里逃逸出来的是孤傲,他光鲜的外表世界后是黑色的寂寞的冷。玲子的那个学生已经无可救药地冲向井,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一直观察着芸芸众生的渡边本人又如何?还不是徘徊在井口边,他甚至在井里生活过一段时期,无法自拔。说到底,这口井利用的不过是人的弱点,人的弱点就是它煮的黑的原材料。每个人都有弱点,所以它的黑是“非常之黑”,所以每个人迟早都会进去。
但是,正因为世上无人完美,世界才显得如此可爱,有些弱点反能传达出人性的温暖。假如是真的,直子臆造出这口井为精神寄托这一点本身就不是纯黑的反应。
这样想来,我觉得煮后的井的颜色应该透出一种灰,而不该是墨黑。
不知我的这番妄言,村上春树先生可赞同?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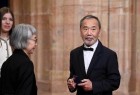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张爱玲与村上春树: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