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日本社会的批判书——「海边的卡夫卡」
《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责任编辑沈维藩:
《海边的卡夫卡》写的是少年的成熟成长……但是,笔者却以为:这是一本当今日本社会的批判书。不信么?且看——
“杀父奸母”,这是何等的弥天大罪,可在本书中,却未见有半点罪恶感。
《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译者林少华:
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潇洒的举止,没有迷人的谈吐,衣着十分随便(他从不穿西装),即使走在中国的乡村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无数日本女性甚至中国女性视为世界第一男人。
《海边的卡夫卡》写的是少年的成熟成长……村上春树如是说。但是,笔者作为中译本的责任编辑(除译者以外读得最仔细的人),却以为:这是一本当今日本社会的批判书。不信么?且看——
“杀父奸母”,这是何等的弥天大罪,可在本书中,却未见有半点罪恶感。
先看这父,亦即“琼尼·沃克先生”。他用“被活活切割开来的生灵的魂”做笛子,还宣称“最后大概可以做成宇宙那么大的笛子”,这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狼子野心的写照么?这样的人,岂不该杀?何况,“琼尼·沃克先生”其实并没有被杀死,而是钻进了代替他儿子——少年田村卡夫卡——杀父的弱智老人中田的体内。中田在二战中丧失了记忆,是一具“空壳”,“和空房子是同一回事,和不上锁的空房子一模一样。只要有意,谁都可以自由进去”,“周围人叫我干什么我就老老实实拼命干什么”,简直就是因战后未作有效清算而感觉日趋麻木的日本民众的象征。“琼尼·沃克先生”可以利用中田的“没有实质”继续作恶,甚至可能让“天上掉下的东西是一万把菜刀、是炸弹、或是毒瓦斯”,他的死是“自愿地死了”,是军国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巧妙遁形。“但我还没进入下一世界。就是说,我是移行的灵魂。移行的灵魂没有形体,我现在这样子不过是临时显形,所以你不可能伤害现在的我”。当然,忧虑深重的作者并没有对民众尤其是青年失去信心,中田最终还是醒悟到了“要返回普通的中田”,而隐藏在中田体内的怪物最终也被中田的后继者青年星野碎尸万段了。
再看那母——优雅的佐伯女士。她早年为了确保她与爱人“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圆圈中”而“导致许多东西扭曲变形”,爱人一死即化为只有过去、没有现在的土木形骸,后来又抛弃了“绝对不可扔掉的”孩子,一如日本近代以来孤芳自赏的知识层,既不能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有所阻止,战后又在民众中逐渐失去了影响,甚至放弃了对民众的引导责任。但是,她的少女时代是“不含杂质的”,她的作品是“和美友爱的世界”、“天赋才华和无欲心灵坦诚而温柔的砌合”,宛然是日本近代优秀文明的化身。惟因如此,少年才“接受她的血”、“渴求她的心”,在她的要求下离开逃避的“森林”返回现实,立志“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也惟因如此,少年与佐伯少女幽灵的“交合”,才读来但见诗意,未有秽恶。
“杀父”——去除民族精神中的恶,“奸母”——是承继民族精神中的美:如此少年,应该是村上理想中的新日本知识者。
不问政治的作家是没有的。我们已经看到了村上在《舞!舞!舞!》中责难“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奇鸟行状录》中审视“扭歪变形”的日本,如果上面那许多的引文还不能令你相信这是一部批判书,那就来听听小说中那位智者大岛——我简直怀疑他是村上的传声筒——对日本民族的棒喝之声:“缺乏想像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的是这些东西。我从心底畏惧和憎恶的这些东西只要有主动承认错误的勇气,一般都可以挽回。然而缺乏想像力的狭隘和苛刻却同寄生虫无异,它们改变赖以寄生的主体、改变自身形状而无限繁衍下去。这里没有获救希望。”
“世界万物都是隐喻。不是任何人都实际杀父奸母。”大岛又如是说。读懂了隐喻,你就读懂了《海边的卡夫卡》。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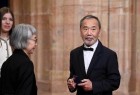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当今日本社会的批判书——「海边的卡夫卡」: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