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阳界与阴界之间(选译)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1987年9月出版以来,上下卷己销400余万部,成为超级畅销书。初版封面的腰封上宣称是“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其后作者则反复强调是“现实主义小说”。(《村上春树全集月报·6》1991年3月)至于何为现实主义小说,村上将其定义为“现实地写现实性事件(中略),当然不必是真事”。(访谈录:《“挪成的森林”的秘密》,见《文艺春秋》1989年4月号)不用说,这一想法是同私小说那种平板式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所谓小说,即是将虚构现实化”。这就是说,村上春树的创作意图在于对虚构——将读者引人作品世界的虚构——赋予现实感。
在访谈录《何以说是“我”的时代》(《Days Japan》1989年3月号)中,村上春树说“现代小说家(中略)必须多少超越现实主义”。并说要以自行准备的“超自然的”,“幻想的”等关键字眼为催生剂来进入“非现实世界”。就《挪》而言,直子栖身不出的深山疗养院即是“完全的神话世界”、“彻底的黑暗世界”。毫无疑问,这部小说的核心就在这座疗养院。
众所周知,《挪》是以短篇小说《萤》(1983年1月)为雏形写成的。改稿之际,“我所考虑的,大体是‘我’将去京都疗养院去找直子”(《长访录》,《Par Avion》1988年4月号)——如果村上所述无误,那么这段话便构成了他初期构思的中轴。《萤》中,相当于后来的直子的患有心病的女子在一夜交合之后,没有告知“我”就进了疗养院,剩下的“我”拿着室友送的萤火虫爬上楼顶天台放飞,故事就此结束。“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萤火虫的光点显然是那个女子的象征。不妨说,《挪》便是从“我”去觅其行踪开始的。
几个月后,接得直子告知其所在地点的信的《挪》中的“我”(己被取名为渡边),第二天很早就动身去京都,乘市营公共汽车来到三条,转乘12时35分驶发的私营铁路电车沿鸭川北上。穿过几处杉树林和村落,在眼界开阔的山顶小憩之后,在斜坡上的汽车站再次下车的“我”走了15分钟,总算见到了疗养院指示牌——这个“我”的行程比其他场面详细得多,并且同现实地理情况相吻合。(中略)
“山中阴界”第一夜,蓦然醒来的“我”发现直子正跪在枕边地板上凝视“我”的眼睛。直子的瞳仁异常靖澈,“几乎可以透过它看到对面的世界”,稍顷,直子脱去睡衣。那沐浴月光的裸体化为完美得甚至使我“感觉不到一丝性的亢奋”的艺术品。这岂不正是阴界神秘的女性形象?翌日,在躺倒在草地上的直子柔软的手指的诱导下,我一泄而出——可以说,我是在接受来自阴界的女子的“治疗”。当然,我无意说“阿美寮”就是极乐净土本身。“完美肉体”的显现需要月夜作为条件,这点从第二天雨夜“直子仍是往日的直子”这一事实亦可看出。另外,正如我继续读《魔山》所象征的那样,亦可视之为“奥尔浦斯(奥尔猜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竖琴名手,在用音乐榕死去的妻子领回家的途中,因犯戒而失去妻子。)式”的黄泉之旅。但结果恐并无不同,对阳界,心存芥蒂之人所去的世界、村上所说的“神话世界”即在这里。“我”虽然为了把直于领回阳界面去阴界找她,但“我”早已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木月之死而认识到“死并非是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水存”。既然如此,就势留在阴界也未尝不可。其最初构思,说不定在此进入尾声。
但是,“我”返回了东京。所以返回,恐怕是由于另一女性绿子的吸引。原定写“三百页稿纸(每页四百字)”的计划结果膨胀成了“将近九百万稿纸”(见单行本“后记”)的长篇。作者说这是“因为想到起用绿子这个女孩而一发不可遏止的缘故”,(《文艺春秋》1989年4月号)若仅是一个直子,大概会成为一部向心力占上风的将“我”拽入一如“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股脑儿煮在里边”的野外水井以及成为《挪》素村之一的《盲柳与睡女人》中“一个劲儿向下伸去(略)而以黑暗为养分”的“盲柳”所暗示的黑暗滞重世界里的小说。
村上已意识到自己身上有“离心力和向心力、积极的力与消极的力”(《Par Avion)1988年4月号)在相持不下,“为了保持平衡而需要一个离心性质的因子,那便是绿子”,作者这样公开了自己的创作秘密。的确,两年前失去母亲现在又在照料因患脑瘤奄奄一息的父亲的绿子,既肃然直面周围的死,又体现眼前的生。这样的绿子对从京都返回的“我”说“活像见过幽灵”实属理所当然。“我”——直子、“我”——绿子这两道流程的相互碰撞是这部作品的基本架构,在此架构下配置了玲子、永泽、初美等外围人物。直子自尽后,和直子在阿美寮同一房间里生活的玲子带着吉他来到我寄宿的地方,弹起直子喜欢的乐曲为直子举行“葬礼”。直子死前留下纸条说“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玲子于是从上到下身穿直子遗物出现在“我”面前。这时的玲子不妨视之为直子的再现,视之为阴界的使者。稍后,两人不顾年龄的差异结合在一起,一共亲热了四次,可以说,“我”是为阴界所动心所诱惑。当时,“我”刚刚结束直子之死带来的长途一个月的流浪生活,心想“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可是,同玲子的交合大概又一次使他陷入了不安之中。在上野站送走玲子后,“我”给绿子打去电话,想和她“一切从头开始”。不料,尽管“我”希望重返阳界,但“我”的声音却未能传给对方。绿子问“我”“现在哪里”,“我”却无法回答,而是“从哪里也不是的场所连连呼唤绿子”。这个结尾想必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20岁的“我”不上不下地悬在阳界与阴界之间。《挪》的时间跨度主要是1968年春至1970年秋。但其外围时间则设定在阿美寮事件发生后经过18年的1987年,即小说印行时,亦即人到中年的“我”在汉堡机场机舱内听见《挪威的森林》受到强烈震撼之时。作品最后反复道:“我现在哪里?”“我现在哪里?”·····
其中加点句乃穿插的外围时间,表明即将迎来38岁的“我”仍未获得稳定的位置。
关于《挪威的森林》书名,村上说“非常有象征意味”,原诗《NORWEGIAN WOOD》“静谧、忧伤,而又今人莫名地沉醉”,(《村上春树全集·月报·6》1991年3月)适合小说里的气氛。关于最后场面,他提示说“只要读一下《ELEANOR RIGBY》和《NOWHERE MAN》这两首歌的歌词(略),我想就可理解其含义。(《Par Avion》1988年4月号)哪一首都是献给直子“葬礼“的歌曲,但正如《NORWEGIAN WOOD》的副标题“This bird hasflown”(小鸟飞走了)以及《ELEANOR RIGBY》中反复出现“The lonely people”(孤独的人们)所表明的那样,亦如《NOWHEREMAN》中“没有归宿的人”所倾诉的那样,这部作品讲述的是怀着深深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往来彷徨的男人的故事。这也是涉及衬上文学基干的主题。
据日本《国文学》1995年3月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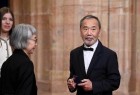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挪威的森林》——阳界与阴界之间(选译):等您坐沙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