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偶像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幽灵
对于自觉或不自觉认同“小资情调”的读者,“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未免有点高大滞重。然而确确实实,这个词语的爱用者乃至发明者是以擅长写“百分之百恋爱小说”著称、并由此被奉为“小资偶像”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舞舞舞》(1)中,“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词至少出现了十一次。对于一部小说而非理论著作,该词的频度堪称突兀。那么,以这个看来与“百分之百恋爱”是百分之百无缘的关键词为洞口,或许能够管窥这位小资作家的另一种姿态。近日(2005年9月23日)笔者以中文google网搜索搜索“村上春树”得1,052,250条,搜索“马克思”(含繁体字“馬克思”)得1,350,000条,两者同位百万巨数而接近。那么把“村上春树”与“马克思”连接起来讨论也并非无理。
与作者大部分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同样,《舞》中主人公也是“我”——“我”是个34岁的单身男性,以写广告文字谋生,对自己的生活与环境经常进行反省思考。在小说中,“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词语无一例外地发自这个“我”,或见于他与别人的对话,或见于他的内心独白。“我”的所思所想无疑投射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倾向。
该词的所指时代大体是1980年以后。《舞》发表于1988年,叙事是现在时地展开。作者有意让《舞》中一位刑警人物强调80年代“现在”与前此70年代的重大区别:“现在不是一九七零年,没有闲工夫和你在这里玩什么反权力游戏。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205页)
“资本主义”通常既可以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使用。前者如卡尔•马克思,后者如马克斯•韦伯。在《舞》中它作为“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词,意味接近前者。且举数例——“犹如巨蚁冢般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24页);“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25页)主人公的自我感觉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来临,自己在这种社会里孑然一身”;(36页)主人公注意到一家超市店的莴苣保鲜时间超乎寻常,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此推断:“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加以特殊训练的结果。果真如此我也决不惊讶——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157页)主人公的老同学五反田在聊天时感叹,“同女人睡觉也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接待费报销,这世道非同小可”,主人公一言而蔽之:“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183页)显然,主人公如此命名他所处的那个“高度”社会,如此不厌其烦、一以贯之地使用这个命名,是在有意地、乃至刻意地显示某种姿态。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术语,通常首先指谓的是一种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以资本为主体,以赢利为目的。在马克思那里,这个生产方式还隐蔽地制约着各种社会观念的表象。《舞》中的主人公对这个基本含义有所发挥:
“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的缺德,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如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75页) 资本的大小决定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资本的牟利性格不以投资者道德善恶为转移;资本是精于计算和善于计划的,因此“公正云云”也按成本推算——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嗅出马克思批判哲学的气息。
“主义”这个词的本义是指某种最高理念,因此“资本主义”也可以是一个聚焦于思想观念或文化领域的概念。《舞》中主人公所关注的看来正是这个层面,他如此发论: “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神话。”(74页)
这番议论的要点是,资本在消解古老神话和旧有宗教的同时又制造了新式神话与新式宗教。而这个论点依然是伸发于马克思的视阈。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过“拜物教”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正是在对宗教信仰的改造中最深刻地表现出它无所不驭的魔力:“要找到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我把这叫做拜物教。”(2)由此看来,主人公头脑中确实徘徊着马克思的幽灵。
这个幽灵在作者身上有迹可寻。在比《舞》早一年发表的《挪威的森林》中,作者特别提到大学生主人公渡边读过《资本论》,赞赏马克思“整体思考”的方法。《挪》的故事发生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渡边当时对60年代末期的激进风潮持怀疑和疏离态度:“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对任何事情都不要想得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3)因为他对当时流行风潮的感觉是:“人们在呼喊变革,仿佛变革正在席卷每个角落。然而这些无一不是虚构的毫无意义的背景画面而已。”(4)这些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挪》中未出现“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话语。而《舞》中80年代主人公却是时时谈论,处处批判,乃至由今思昔而感叹“令人怀念的六十年代”,(186页)甚至一百八十度转弯地赞叹那个“时代真是好极了”。(75页)如果说《挪》与《舞》中两位主人公都有作者本人的投影,那么后者的转变自然应从日本80年代“高度发达”的新背景中寻求解释。
这个新背景有何特征呢?或者说,作者所力图表现并批判之的《舞》中世界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呢?我们以《舞》中主人公的若干独特评语为透视点继续管窥。
“犹如巨蚁冢般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犹如巨蚁冢般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一份工作不算什么难事。当然,我是说只要你不对工作的种类和内容过于挑剔的话。”(24页)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巨蚁冢”的比喻,它把“高度发达”的社会整体首先形容为巨大的蚂蚁群。我们知道,在蚂蚁群中,每只蚂蚁都有工作,每只蚂蚁也都能获得食物。因此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谋生与温饱已经不成问题,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过的“饥寒交迫”已经成为历史。蚂蚁群还是个内部相互合作的群体,这也意味着长期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之类的阶级矛盾矛盾,至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不可调和,存亡攸关。当然,这仅仅是就“蚂蚁冢”社会内部而言,主人公并没有忘记提醒读者,世界上还有孟加拉和苏丹那种另类的非发达地区。(25页)
蚂蚁群组织严密,其中绝大多数是工蚁,它们类同划一,步调整齐。因此这个比喻还提示了现代大众社会的另一特点:个体如同社会大机器中被迫运转的一个零部件。主人公有很强烈的个体意识,对周围人群“言行举止无非老套数”的光景格外敏感,即使在咖啡馆喝咖啡时也会“产生一股铭心刻骨的强烈孤独感”,觉得“惟独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局外人”。(35页)《舞》中另一位善于适应环境而颇有名声的演员五反田则如此感叹自己的处境:“我是没有选择自由的,什么也选择不了。就连自己领带的花纹都几乎不容选择。”(397页)五反田的职业是面对大众传媒进行表演,因此他的“没有选择自由”的处境具有“大众”的代表性。五反田还如此自我调侃:“有一种人以为只要把价格昂贵的名牌产品搞到手,就可以与众不同,却意识不到惟其如此才到头来落的得个与众相同。”(361页)
“巨蚁冢”的中心词是“冢”;冢者,大坟也。“巨蚁冢”把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容为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巨大蚂蚁坟冢,这个比喻显然包含了作者的评判。马克思老人家曾经以“异化”和“物化”批判资本主义,主人公这个当代新人的“蚂蚁冢”比喻可谓青出于蓝而浓于蓝。
“浪费是最大的美德”
当代学者通常把欧美70年代以后的社会称为“消费社会”,《舞》中主人公则把“消费”改称为“浪费”:
“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25页)
“假如大家杜绝一切浪费,肯定发生大规模危机,世界经济土崩瓦解。浪费是引起矛盾的燃料,矛盾使经济充满活力,而活力又造成新的浪费。”(34页)
“浪费”成为最大美德,这大体确是资本主义社会前所未有。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出现过新教伦理,其基本德目是提倡“禁欲”和“节俭”。马克斯•韦伯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必然要求,“强迫节省的禁欲能够导致资本的积累”。(5)因此,主人公以与新教所尚相反的“浪费美德”解释“高度发达”,可谓搔到痒处。“浪费”与“消费”一字之差,却包含着迥然相异的价值判断。主人公何以如此贬斥“消费”?且听他对文化产品的评价:
“真正好的东西少之又少,书也好电影也好音乐会也好摇滚乐也好。听一个小时收音机至多能听到一支好的,其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垃圾。”(138页)
“我们一面同音乐,一面在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如此做法,带来的结果无非是加速空气污染,使臭氧层遭到破坏,噪音增多,人们神经紧张,地下资源枯竭。”(143页)
文化产品大批量涌出应该是皆大欢喜之好事,而主人公却认为这一切对消费者和生存环境都造成恶果。小说中提出的一个例证是演员五反田,他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消费能力,而他的苦恼感却超出一般:“问题是没有生活”,(181页)“这世道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可捉摸,连自己是穷鬼还是富翁都搞不清。东西琳琅满目,想要的却没有;尽可挥金如土,想用钱的地方却没得用;漂亮女郎召之即来,而喜欢的女人却睡不到一起。莫名其妙的人生!”(279页)用一句套话表述,他也许可谓是“物质的富翁,心灵的穷鬼”。因此他对消费社会的反思甚至比“局外人”的主人公更为痛切:
“我所处的就是这么个世界,以为只消把港区、欧洲车、劳力士手表拿到手就算一流。无聊透顶,毫无意思!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必要性这玩意儿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其实无非是把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涂抹上十分需要的色彩。容易得很,只要大量制造信息即可。住则港区,乘则宝马,戴则劳力士——如此反复宣传,于是大家深信不疑。”(361页)
马尔库塞在《单维人》中指出,消费社会的重大特点是通过媒体广告等方式制造大众的“虚假需求”,它是“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它制造的是“一种不幸中的幸福感”,最流行的虚假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6)村上春树所针砭的“浪费”现象看来与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之说遥相呼应。马尔库塞《单维人》写于70年代,村上春树《舞》写于80年代,后者很可能接受了前者。
“文化扫雪工”
主人公将自己写广告文字为生计的职业调侃为“文化扫雪工”:
“三年半时间里,我始终在做这种兼带文化性质的工作——文化扫雪工”,“这同收垃圾扫积雪是一回事”。(17页)
这里需要略作辨析——扫雪通常被视为低贱之活,是没有文化知识的普通人所干,而主人公特别在乎自己“普通人”的身份。小说中他唯一吟唱过的一首歌题名为《普通人》,歌词曰:“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你我彼此不难分难解。虽然干的活计不一样,但同样平平庸庸默默无闻。哎呀呀,我们都是普通人。”(271页)显然,“文化扫雪工”这个比喻的意味不在于轻视普通人的“扫雪”之类工作,而在于反讽“带有文化性质的工作”。这个尖刻比喻把“文化”的灵光无情地抹去了。——“文化扫雪工”这个行当甚至与妓女的谋生方式并无二致,在与一名高级俱乐部的应召女郎相会时主人公作如此感想:“我干的是所谓文化扫雪工,她干的是官能扫雪工”。(186页)
主人公的自嘲首先出自他对广告生涯的厌倦:“我写的稿件,估计有一半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无济于事,纯属浪费纸张和墨水”。(25页)在他看来,广告行当不仅是浪费,而且毋宁说是制造灾祸。他以替美食店写广告文字为例:“那工作毫无意义可言。……被你介绍过的那家饭店,随着名气的提高,味道和服务态度反倒急剧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142页)如此贬斥广告功效,在我们看来未免片面至极。但是主人公有其逻辑:广告是连接资本赢利与大众消费的桥梁,既然大众“消费”已经成为大众“浪费”,那么广告制造的就不是“消费”需求而是“浪费”欲望;调侃广告是批判“浪费”的逻辑结果。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在分析他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提出:“市场也有其乌托邦”。(7)这意味着广告不仅是广告,它在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还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确实,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如果没有广告就难以维持运转,这个不争事实足以说明广告在制造社会意识过程中功能巨大。无论主人公是否意识到,其对广告的尖刻嘲讽看来并非徒放空枪。
主人公以“文化扫雪工”而非“广告扫雪工”自嘲,这表明他针砭的不仅是广告之类。例如主人公还谈论过与广告同属传播媒体的新闻报道。小说一开始就述及一个大资本集团吞并小宾馆的事件,*纵者不仅利用黑社会势力,而且与政府部门暗中勾结。主人公读到该事件报道后的评论耐人寻味,他一方面肯定这个报道揭露的是“黑幕”,报道本身“材料详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另一方面却断定它“落后于时代”,因为“这等事已经算不上什么黑幕,而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程序。”(75页)这个评论提示了消费时代“文化”的另一特点——事实和正义不再是被公认的新闻报道要素。《舞》中一位作家人物牧村的议论印证了这个变化:“很久很久以前,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心里一清二楚”,“可现在不同,所谓正义云云,谁都不懂。所以只好应付好眼前的事。”(243)作者由此向读者强调,在这个“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不仅新闻报道,而且文学创作之类也不再需要“正义云云”了。
“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
在主人公看来,甚至哲学也发生了划时代变化:
“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75页)
如果说广告直接属于资本的牟利活动,新闻报道天然地贴近牟利活动(它与广告同以大众传媒为载体),那么哲学则应该属于“更高地漂浮在经济基础上空”(恩格斯老人语)的形而上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类似经营学”表征了“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深度。主人公本人的哲学倾向是不识时务地迷恋于“思维体系”,他因此受到一名绰号“文学”的警官的善意劝告:
“思维体系?那东西没有多大意义,和手工做的真空管扩音器一个样。与其花时间费那个麻烦,不如去音响器材商店买个新的晶体管扩音器,又便宜音质又好。现在不是议论什么思维体系的时代。那东西有价值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今天不同。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得到。买个合适的来,拼凑连接一下就行了,省事得很。……假如拘泥于什么思维体系,势必被时代甩下。” (248页) 主人公转而期望在美学想象的天地中保留一片“思维体系”的净土,然而令他愤懑而无奈的是,时代的经营学动力也大面积地驱使美学想象力改变方向:
“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从所有的空隙中发掘出商品来。一旦产生幻想,势必作为纯粹的商品开始发挥作用。幻想,此乃关键所在。卖春也罢,卖身也罢,阶层差别也罢,个人攻击也罢,**性欲也罢,什么也罢,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装,贴上漂亮的标签,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350页)
詹明信有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显著标志是审美成为赢利目标:“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8)至此我们可以确认,《舞》中主人公的舞蹈姿态与欧美左派学者们的理论实在是异域同步,形离神似。
再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何以先前钟情于写“百分之百恋爱小说”的村上春树会有如此批判姿态?为什么如此激越姿态依然可谓属于“小资情调”?我的理由是,首先,在当代语境中,“小资”意味着小有资产(包括文化知识财产),自食其力,不虞温饱。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无论是“高度发达社会”抑或前此的“小康社会”,多数人或已成“小资”,或正期望成为“小资”。村上春树本人辛苦经营过咖啡小馆,后来以写作技能的文化资产谋生,无论其想象力如何腾挪跳跃,都可谓不折不扣的一个“小资”人物。其次,小资情调的特色在于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率性而游,率情而爱。而这个境界有赖于无虞温饱的“小资”生活条件。《挪威的森林》中渡边与绿子们之所以能够沉浸于“百分之百的恋爱”,原因首先在于他(她)们的谋生条件已然进入“小资”境内。这里不妨赘言:假如人人都成为小资,那倒是庶几接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之境界。但是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增殖才是社会主流目标,自由自在的小资情调随时随处可能遭遇资本逻辑的驱迫而异化为它由它在。例如,《挪》中的永泽为奋斗体面“绅士”目标而离弃他喜欢的恋人初美,最终导致初美自杀(他的“绅士”定义是:只做应该做的事。不做喜爱做的事);《舞》中的“成功人士”五反田悲叹“漂亮女郎召之即来,而喜欢的女人却睡不到一起。莫名其妙的人生”,他本人最终投海自尽(他醒悟后对所谓“成功”的反思是“其实无非是把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涂抹上十分需要的色彩”)。这两个人物可谓是有小资身份而乏小资情调的代表。由此看来,“百分之百恋爱”的小资情调在“高度发达”社会中难免大打折扣,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走向反面。那么,从前者的立场疏远乃至警戒后者也就不能视为一种另类姿态,而毋宁说也是出于百分之百小资情调的率性所为。
顺便一提,激烈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詹明信在一篇论文中承认,他归根结底还是从属于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员(9),虽然这个定位不无自视过高的嫌疑,倒也接近村上春树《舞》中主人公的想法:“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得在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74页)那么,把村上春树《舞》中的批判姿态归为“小资情调”的别一种舞姿应是合情合理的吧。
注释
(1) 村上春树《舞舞舞》,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6月。本文引涉皆出该译本。
(2) 马克思《资本论》,《马恩全集》25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3)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第25页,林少华译,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4) 同上,第258页。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与资本主义精神》165页.,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6页,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7)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32页,王振逢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8)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62页,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9) 詹明信《时间的种子》第65页,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
(本文初发于上海《文镜》杂志,2004年8月,略作修改)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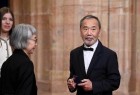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新年快乐~
渡边君!!!新年快乐!!!又是一年,希...
发现了一片心灵的自留地~
好棒的站点!从zlibrary上下了《1Q84》...
2024年11月24日,在这个网站上读完第七...
会不会有林少华的译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