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暖凄凉的葬礼
我是在摇晃的电车上看完《挪威的森林》的。
黄昏真长的可以。最后一缕阳光的余烬暗淡的泼在书页上,渡边和玲子相互拥抱,彼此抚慰。一只白猫在深灰的夜里倏然而过,耳边传来樱花怒放的声音,仿佛BETTLES的歌声响在寂静中的某个地方,一场温暖而凄凉的歌声的盛宴埋葬了直子和年少的爱情。
这是村上春树式的结尾。从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看到渡边在51首歌声后结束这个故事,而不是在某个不知何处的地方连连呼唤绿子。渡边好象是身处在一场大雾中,失聪,失明。茫无目的。直子是一点流萤般的微光,伸手却永远不可触及;绿子则不知从何处蹦入渡边的世界,带着清新的爽气使他振奋,绿子是切实而温暖的,然而正是这种实在使渡边恐惧;在直子和绿子之间,生着好看皱纹的玲子则成为桥梁,渡边借助她得以在梦境和真实之间切换,渡边与玲子最后的交合是渡边告别青春的仪式。
生命在村上看来就是一场梦中之梦。就是一次在虚无中与虚无搏斗的惨烈战事。你始终离地面相距十几公分,落不到实处,心里空空的无所凭借。唯一的生机就是在漂浮的过程中手舞足蹈地抓住的另外一个人--一根同样漂流的稻草。直子就是渡边拼命想要抓住的一根稻草,一丝握不住的风,她在渡边的手心留下的只有空气流动的温度,带着些阴冷的潮湿和惆怅。直子的死是必然的--她并不爱渡边,渡边或许只是她想要保留的某种不能舍弃的东西的媒介,通过他直子可以走到往昔的岁月中去,再见木月。在记忆残片中,直子的生命恍惚的穿过一扇扇门,在任何地方都不作停留,终于消失在森林尽头那幽暗的黎明时分。本月、直子、渡边,他们是互为因果,互相吸附的,像几个重叠显影的幻像,一个存在消失了,依赖其幻像生存的另一个也被削薄,隐约出透明的生命底色,最终跟着消逝,似乎是一连串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在追合的循环圈内宣告生命的无奈与空茫。
死与性,也不过为一种证明。渡边在等待直子的百无聊赖中与素不相识的女子交合;泽毫无心肺的到处寻欢作乐,把自己当作一架不会磨损的性爱机器,在机械爱欲中提升生命意义;渡边与直子的第一次交欢,直子有世界上最凄楚的呻吟--性爱并非是快乐和享受,而是无依无靠的灵魂追逐可见光芒时的痛苦与代价,是人向世界伸出试探的触角,纵身与其中只为证明生的存在与合理。当爱欲终究不能抚慰和填补生命中那与生俱来的黑洞时,终于别无选择的走向死亡。木月如此,直子也如此,在村上书中一个个死去的人,莫不如此。这黑洞是魂无可归的焦虑和渴盼,还有彻骨的冷漠与疑惑。对于渡边,木月的死让他硬生生的剥离了对现实世界的信赖,窥见生命的空幻与不可捉摸,使他过早的告别少年,陷入孤寂与怀疑;而直子的死则使他重回现实世界的梦幻彻底粉碎,如同击向虚空的一记重拳,撞碎的一切不仅仅是空气,而且使渡边早已经变形的像布满裂纹的玻璃一样的内心,碎得无可收拾。纵然有鲜活的绿子,也不可能拯救这齑粉的必然命运,何况绿子,本身也是一株车辙缝隙里辗转的草,根本无力承负渡边茫然的灵魂。
于是我在《挪威的森林》里听出了深重的叹息,那决不是一个忧伤可以形容。若有堂吉诃德似的人物同风车作战,等待他的恐怕是世人的嘲笑,同空虚抗争的人永远是寂寞的英雄,孤独的疯子,逆风前行的人是悲哀的。“我们只是在时间之中彷徨,从宇宙诞生直到死亡的时间里。所以我们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只是风。”我们哪儿也去不了,惟有爱,能给这漆黑的底色上涂抹一些光亮,那也是一瞬而过的流星,光芒落尽之后愈发现出无尽的黑暗,一辈子的时光就在其中穿行,慢慢咀嚼,一点一滴都是苦涩。
我们终究都是要死的。我们回首相望的时候,只是在一盏灯里看见逝去的容颜,我们伸出手去,仿佛要挽回那失去的时光。然而那光总在眼前徘徊,看得到,摸不着。一块积满灰尘的毛玻璃,将我们与幸福永远隔开。
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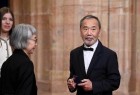


一个温暖凄凉的葬礼:等您坐沙发呢!